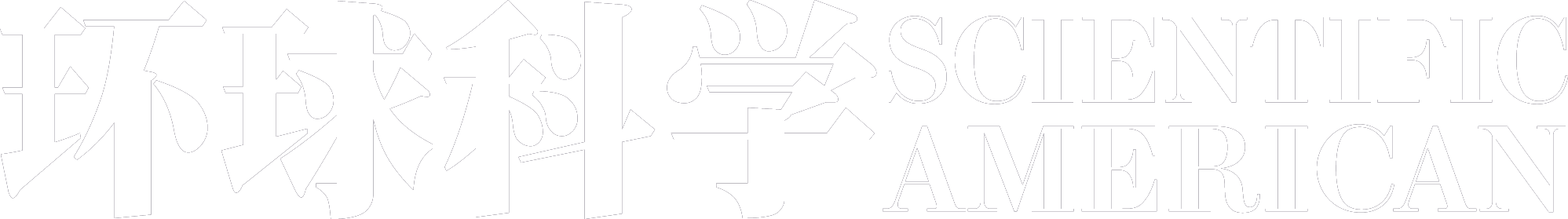一百年后的人们,会觉得现在的我们很荒诞吗?撰文 | 马东源
审校 | 二七
1985年春天,一位名叫杰弗里·劳森(Jeffrey Lawson)的早产儿降生在美国华盛顿。但由于他的肺动脉导管未闭,医生需要立即手术。
令人震惊的是,在手术全程,医生都没有使用麻醉剂,只使用了泮库溴铵(pavulon)——一种肌肉松弛剂。这种肌肉松弛剂可以让杰弗里在手术过程中不乱动,可意识却一直清醒。
“医生首先在杰弗里的颈部开了一个小口,然后把一根管子从这个小口伸入到胸腔中。接着从胸骨到脊柱做了一个切口,然后将杰弗里的肉、肋骨和一个肺拉到一边,并对血管进行手术。缝合胸腔后,医生又在侧面开了另一个口,把管子插进了他的肺部。” 1991年发表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了手术的过程。
显然,尽管不能动,但当时还是个新生儿的杰弗里应该清楚感受到了脖子开口、管子插入体内、胸膛被剖开又缝合上的整个过程。

在手术后,杰弗里出现休克,心脏、肾、肝等多脏器开始衰竭,最终于5周后死亡。直到手术的几个月后,杰弗里那悲痛欲绝的母亲才得知自己的儿子在手术时没有打麻药,当她去质问做手术的医生为什么不使用麻醉剂时,医生说:“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婴儿能感受到疼痛。”
看到这,或许你会觉得我只是在讲一个无良庸医的故事,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个例。关于“婴儿没有痛觉”这一认知,某种程度上,在当时甚至可以算是一种医学常识。很多医生在给婴儿做手术时,都不会使用麻醉剂或只使用很少量的麻醉剂;而就算使用了麻醉剂,他们的出发点也只是为了让婴儿在手术过程中不要乱动,而非减轻婴儿的痛苦。这种对婴儿的偏见,其实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
否认婴儿痛觉的漫长岁月
那么就让我们将时针再往回拨一百多年,回顾一下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婴儿没有痛觉。
19世纪中期, “科学家”(scientist)一词都才出现十多年(1833年出现),那时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常识去评判,在某些方面,用“无知和荒诞”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疼痛”的认知。
1842年,医生克劳福德·朗(Crawford Long)首次在人类手术时使用了麻醉剂,标志着人类麻醉史的开始。然而,麻醉药品刚出现时却并未受到所有人的推崇。因为在那时,大家普遍还认为疼痛是有益的, “感受到疼痛表示健康”。一位叫做费利克斯·帕斯卡利斯(Felix Pascalis)的美国医生在1826年写道:“感受痛苦需要健全和健康的器官。因此,我们的公理是,痛苦越大,我们对生命的能力就更有信心”。受这种信念的影响,还有不少人反对使用麻醉剂。
直到几年后,人们才开始普遍接受疼痛是不好的、需要被缓解的——当然,仅限于会说话的成年人,而对于婴儿,不少人甚至可能觉得那是另一个物种。1859年,在麻醉剂出现十多年后,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这带给了许多人一种朴素的观点:人类是从更低等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

受达尔文主义影响,一些人将新生儿定义为一种还未完全进化的“亚人类有机体”,是人类进化早期的一种生命状态,和动物的地位差不多。因此,婴儿的感知能力,也同时被忽略和否认了。1873年一位叫做艾尔弗雷德·根茨默尔(Alfred Genzmer)的研究者,用针头扎婴儿的鼻子、嘴唇和手,试图探究婴儿是否有痛觉。尽管观察到了婴儿眼眶湿润这样明显的现象,他仍然总结道:“婴儿对疼痛的感觉很明显未发育完全”。对于婴儿眼眶湿润这个观察结果,他直接将其解释为“不相关的现象”。
根茨默尔的解释或许会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时的人们对于人类内在感知的认知还近乎为零。虽然在那时心理学已经开始萌芽,但距离它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研究人类内在感知的科学形式(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还有约莫一个世纪。在这个背景下,根茨默尔没有将“眼眶湿润”这一外在现象和“感到疼痛”这一内在感受联系起来,也不足为奇。
随后,“认知心理学”的前身——“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诞生(大约在二十世纪初期),更是让后来的研究者对婴儿的误解开始变本加厉。
“行为主义”只关注人类外在的行为,而完全“拉黑”了内在的意识和感知。“行为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约翰·B·沃森(John Broadus Watson)宣称,心理学是“属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存粹客观实验科学分支”。在“行为主义”潮流的影响下,更多的科学家开始认同:婴儿面对针刺等疼痛刺激,即使是出现了明确的疼痛反应(如哭泣),也与婴儿是否感觉到疼痛无关;它只是一种简单的反射(reflex),是对刺激的自动反应。

“科学权威剥夺了婴儿的哭声,将其称为‘随机声音’;剥夺了婴儿的笑容,将其称为‘肌肉痉挛’或‘气体’;剥夺了婴儿的记忆,将其称为‘幻想’;剥夺了疼痛,将其称为‘反射’”这是后来一位科学家大卫·张伯伦(David B. Chamberlain)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下的句子。
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的研究者对婴儿进行了许多在我们现在看来极不人道的实验,如针刺、电击、热水烫等;而婴儿对此展现出的哭喊、闪躲的动作、痛苦的表情等,统统被“行为主义”潮流下的研究者们解释为简单的、自动的、与是否感觉到疼痛完全无关的反射。
虽然现代神经科学、脑科学等的雏形在这个时候也差不多该开始发展起来了,但那时的神经科学不仅对婴儿痛觉的认识没有太多正向的贡献,反而被研究者继续利用起来否认婴儿的痛觉。科学家认为所有的感觉都集中在大脑皮层,而由于婴儿大脑皮层发育不完全,所以婴儿感受不到痛觉。
曼德尔·舍曼(Mandel Sherman)和艾琳·舍曼(Irene Sherman)夫妇在1936年针对婴儿的针刺实验中总结道:“(婴儿的)交叉屈曲反射(flexion reflex)只在脑干水平进行,并由脊髓和颈髓介导”,并以此作出结论:婴儿应该被视为“亚皮质动物”(sub-cortical animal),因为其对疼痛的反应只依赖于大脑最原始的部分。
接着,心理学家默特尔·麦格劳(Myrtle McGraw)通过对75位婴儿进行的2008次针刺实验发现,出生时间越久的的婴儿,对针刺的反应更强烈,有些新生儿甚至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的反应,她将其解释为大脑在发育过程中与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她总结到:“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有理由认为,新生儿的感知运动反应(sensori-motor reactions)不会超过丘脑水平。”
沉寂
麦格劳的研究得到了当时很多研究者的认可,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对于婴儿是否有痛觉这一问题,在科学界似乎已经盖棺定论。医生普遍默认“婴儿对痛觉的敏感程度很低”这一结论,在手术过程中也往往只对婴儿使用肌肉松弛剂或者很微量的麻醉剂。

但表面的沉寂并不代表这个世界对婴儿的误解将永远持续下去。随着观察和研究的深入,婴儿对于痛觉的反应如此明显,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婴儿没有痛觉”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一些反对的声音开始出现,并为大家对婴儿痛觉的最终发现做好了铺垫。
就在麦格劳的研究成果发表不久后,德国的神经科学家阿尔布雷希特·派佩斯(Albrecht Peiper)就质疑了麦格劳的实验结果和结论。他在自己的实验中发现,出生时间较短的新生儿,对于疼痛的反应虽然更迟钝,但他们终究还是会做出反应,并且不像麦格劳实验中描述的那样轻微。而且对于麦格劳实验中缺乏疼痛反应的婴儿,派佩斯认为这可能与疾病有关,而非正常现象,因为在他的实验中,在健康婴儿和早产儿身上总是能观察到可测量的疼痛迹象。
后来派佩斯在《婴幼儿时期的大脑功能》(Cerebral Function in Infancy and Childhood)一书中写到:“成人可以保留自己在外科手术中免受疼痛的权利。由于婴儿对疼痛的敏感性,他们也理应拥有同样的权利。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当他们的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毫无反抗能力。外科医生宣布婴儿对疼痛并不敏感,并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幽门痉挛手术——这是我亲眼所见,这样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日常经验和科学知识。”
可惜,派佩斯的研究在那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澜,他在学界的影响力也与麦格劳的研究相差甚远(一方面原因是派佩斯的论文是用德文发表的)。之后也有零星的学者提出婴儿可能拥有痛觉,但好像也都石沉大海。不过他们的努力肯定不是无意义的,婴儿“呼痛”的权利正等待着一个爆发点。
爆发
让我们回到1985年7月,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新生儿——杰弗里·劳森去世4个月之后。杰弗里的母亲吉尔·劳森(Jill Lawson)仍然每日以泪洗面,沉浸在失去儿子的悲伤中。那位医生对于手术不打麻药做出的令人费解的解释,在吉尔的脑海里反复回荡,悲伤裹携着愤怒,让她不愿就此放手,她觉得她该为自己死去的儿子做点什么。
吉尔·劳森最终选择了抗争。尽管杰弗里已经逝去,但她还是想要这个世界给自己儿子一个公道。她开始疯狂写信,给专家、给媒体、给任何可能相关的人。或许科学家可以“看似合理”地通过实验结果来解释说:婴儿没有痛觉;但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这永远不能接受。就算在孩子出世之前,母亲也能感觉到自己肚子里那个生命的温度,甚至知道他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舒服,对于“婴儿没有痛觉”这一点,吉尔不可能接受。
在吉尔的努力下,她的故事终于被报道了出来,最有影响力的报道是1986年发表于《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的文章“没有麻醉的手术:早产儿能感受到疼痛吗”(Surgery Without Anesthesia: Can Preemies Feel Pain?)。至此,研究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自娱自乐”式观点,才终于被普通大众了解。这是母亲们向科学界下的战书,吉尔和众多支持者一起,通过媒体的手段要求医学界停止在不打麻药的状态下对婴儿进行手术的行为。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科学界对婴儿痛觉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彼时还是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博士研究生的坎瓦吉特·辛格·阿南德(Kanwaljeet Singh Anand),首先通过血液激素水平的检测,证明了在不麻醉的状态下,普通婴儿和早产儿在手术后会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接着他又发现,相较于使用了麻醉药品的婴儿,未被麻醉的婴儿在手术后恢复的时间更长,同时会出现更多的术后并发症。随后他由很细致地通过行为、面部表情、生理状态等方面的观察,证明了婴儿能感受到疼痛这一事实。

吉尔·劳森的努力和阿南德的研究成果,让社会和科学界都开始重视对婴儿痛觉的认知。这之后关于“婴儿拥有痛觉”的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在1981-1990年间,就有2966篇关于小儿疼痛(pediatric pain)的研究文章发表(相比之下,1950-1980年的30年时间内,满打满算也就只凑得出几十篇相关研究)。1987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和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宣布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对婴儿进行手术不再符合道德标准。
至此,人们对婴儿痛觉的否认终于告一段落。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由得感慨这是多么荒诞。然而,对事物的认知很多时候没办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观察和实践,才能发现一些从前没有注意到、或者被误解的东西。那些曾经在不麻醉的情况下对婴儿进行手术的医生,也不是没有人性的怪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不能保证麻醉药品对婴儿的安全性。医生的出发点仍然是救死扶伤,而不是残害生命——他们只是不知道婴儿会感到痛苦罢了。
就算在十年前,很多人也难以相信世界上会出现一种,可以写文作画、和人对答如流、知识渊博的人工智能技术。世界在变,我们的认知也在变,现在我们嘲笑一两百年前的荒诞;殊不知,我们或许正生活在一百年后人们会认为的荒诞之中。
参考链接
- http://members.tranquility.net/~rwinkel/MGM/blog/chamberlain.html
- https://academic.oup.com/book/24981/chapter-abstract/188919708?redirectedFrom=fulltext&login=false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3548489/
- https://opentext.wsu.edu/psych105/chapter/6-2-a-short-history-of-learning-and-behaviorism/#:~:text=Behaviorism+is+largely+responsible+for,Pavlov+(1849%E2%80%931936).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879174/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890834/
- https://psychclassics.yorku.ca/Darwin/infant.htm
- http://www.cirp.org/library/pain/anand/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17037/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lifestyle/wellness/1986/08/13/surgery-without-anesthesia-can-preemies-feel-pain/54d32183-8eed-49a8-9066-9dc7cf0afa82/
-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1-10-28-mn-378-story.html
- https://www.ox.ac.uk/news/2015-04-21-babies-feel-pain-adults